古籍“御医”张平
他曾主持修复《永乐大典》,认为每册古籍都有浮沉命运和不凡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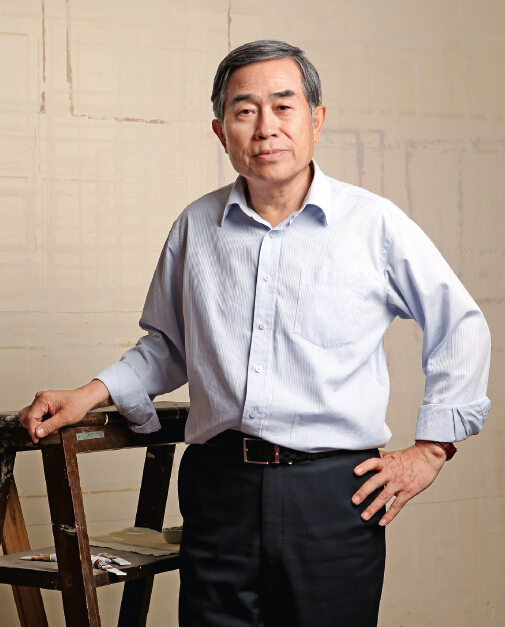
2016年5月16日,张平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修复室接受专访。(《环球人物》记者 傅聪 摄)
人物简介:张平,1953年生于北京。原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修复组组长,主持修复馆藏《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贵文献,著有《古籍修复案例述评》《中国古籍装具》等。
经过层层安检,《环球人物》记者进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一楼尽头处,宽大如厂房的办公间让人豁然开朗。一个个作业台排列其间,毛刷、糨糊、书槌、放大镜、照明灯等工具摆放其上。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或小心翼翼地拿着泛黄的书页细致黏合,或认真剪裁着因补衬而多出来的纸边。一些空置的桌上摆放着大约20×40cm见方的大理石板砖,平整地压在补过的书页上。
这里,就是古籍馆的修复室,近10位修复师正埋首于故纸堆中,在灯下如外科医生般细致地对古书进行着揭、拆、压、包、订……“枯灯独坐”“皓首穷经”,是记者最直接的观感。但在古籍修复师张平眼中,每册古籍都有着沉浮的命运和不凡的由来,而他们这一职业,既融入了考古的厚重,也有医生的缜密,甚至还要有双美学家的眼睛。
张平已经做了近30年的古籍修复工作,曾是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组长,现在已经退休。言谈间他始终不疾不徐,大概正是做这行磨砺出来的“慢性子”。“干这行要有匠人精神,要精益求精,总感觉这样才对得起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贝。如果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
早期依赖经验传承

修复师在补书页。
“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清代《装潢志》中的这段话,是对修复师最形象的比喻。如今已成古籍“御医”的张平,早年也是半路出家。
由于“文革”浩劫,张平的正规学校教育止步于小学毕业。动荡的岁月中,他虽在中学待了一年零一个月,“但都是学工、学农、学军,真正学到的文化知识少得可怜”。19岁,他就进入北京第二印染厂,成为一名模型工。在此期间,张平并没有荒废文化课的学习,他报名参加全国自学考试,最终通过了哲学、逻辑等课程。
曾有一段时间,张平觉得这份模型工人的经历对他的人生毫无裨益,但如今想想,并非如此。“因为模型就是让你首先要会看图纸,我们是木模型,既要懂得铸造技术又要懂得木工技术,所以对于我的动手能力有很强的磨练。”
这份磨练在日后派上了用途。上世纪80年代,张平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师从于馆内著名的“三肖”之一肖顺华(另二人为肖振棠、肖振邦)。“他们同为肖氏家族,不光会修书,还懂书。所以,如果像他们一样懂古籍,会修得更好。”古籍馆的另一位享有盛名的是与“三肖”同时期的“国手”张士达,他原先是琉璃厂的古籍修复师傅,鲁迅、郭沫若等诸多文化名人都曾慕名找他修古书,后来被古籍馆延请,培养了一众仍活跃在国内的古籍修复大师。
张士达、“三肖”等师辈们的修复功力让张平叹服不已,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当属国宝古籍《赵城金藏》的修复。这是一套金代佛教大藏经,共计约7000卷。当它经历战火,被辗转运到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时,因为长期遭受水浸,近一半的经卷已是面目全非:许多经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无法打开。有的长满黑霉,还有的一碰即碎。
面对这令人一筹莫展的局面,师傅们的解决方案却举重若轻:一个字——蒸。将这些粘连在一起的经卷用宣纸包好,再包上一层毛巾,放入柳木笼屉里,像蒸馒头一样地蒸。这样,表层的经卷纸张可以被蒸汽慢慢润松,但又不会被水滴浸泡。每蒸几分钟,就取出经卷,用针或镊子慢慢地将其表层松软的部分一点点挑开,直到挑不动了,再放入笼屉蒸。这样循环往复,直到经卷全部被揭开。这项国内第一个大型文物修复工程开始于1950年,到1965年完成,前后用时16年。
那时,古籍修复就是简单的“师承”,修复手段也一代代沿袭下来。上世纪90年代,张平和同事杜伟生曾前往大英博物馆帮助其修复敦煌遗书。他们见到了对方馆里的一台纸浆补书机,这台机器对于纸张拉力比较好、虫蛀较多的书页修复效率特别高,一张千疮百孔的古宣纸,浸入带糨糊的水里,在机器的自动控制下就可修补破洞。回国后,杜伟生和有工厂经验的张平等人一道潜心钻研,用3年时间设计出适合中国纸张的纸浆补书机,这一发明还获得文化部科学技术进步奖。
那趟英伦之行,让张平开始反思国内古籍修复仅凭经验传承带来的问题。“首先是从业人员的教育差距,咱们的修复人员,像我师傅是高小毕业,我们后来也就是自学到大专。但英国从事修复的起码是本科,还有硕士博士。这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就是如何看待古籍修复工作,它是不是纯技术的,里面有没有科学?”张平的回答是,“这是门科学,肯定是。”
当前古籍修复中依然有不少待解问题,“比如书页出现黄斑,慢慢纸张就降解了,一点力度都没有了,最后就分解粉碎了。后来,我们研究发现,黄斑的出现是因为这些纸张里含有一些金属离子,受潮后生成锈斑。就像钢铁生锈腐蚀,慢慢强度就没有了,纸张也是一样。这种现象如何修复,现在还解决不了,只能留给未来的课题了。”张平说,“将来年轻人的任务还是很重的,这一行可不是单纯的修修补补。”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修复师在小心翼翼地涂抹糨糊。
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而古籍修复出现的时间,按照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起自五代十国时期,当时的和尚道真曾组织人对佛经进行修复。
谈起古籍修复的过程、手法,张平如数家珍,“如同医生给病人建立病例档案,修复古籍首要的一步,就是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确定修复方案,如果修补方案不科学,会对文献造成二次破坏。”其中,制定方案的过程就像“会诊”,会聘请古籍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同为古籍诊断开方”。
之后便是固定的修复套路,“遇到霉烂古籍,要先用同色纸将破损处补齐,然后用排笔在书页背后刷上糨糊,再裱上一层薄棉纸,拂拭平整,逐页依此进行。”“虫蛀书籍,先将要补的书页有字一面向下放在隔板上,在蛀洞周围抹上糨糊,用配好的同色纸对顺纸纹,按在蛀洞上,用左手按住,用右手依糨糊湿印把纸撕下即可。”
受潮严重的书籍,极为脆弱,哪怕轻轻呼一口气都会让纸张碎开,“修复师要戴上口罩,不能喘气,旁边也不能有人走动。”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向来是书画修复行业的准则。经过世代总结,修复师为古籍修复立下了“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四大修复原则。
在由他主持的《永乐大典》的修复中,“最少干预”原则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保护《永乐大典》的原始装帧,修复师在修补书页时创造性地运用“掏补”办法,即在不拆掉书皮和纸捻的情况下,把毛笔和补纸伸进书页中间修补破洞。事先还需精细地将补纸四周的纸毛去掉,降低其和书页搭接处的厚度。
“为找到与《永乐大典》原书皮一致的丝织品,国图的10位修复人员随身携带专用放大镜,在北京各个绸布店搜寻,最终在老字号瑞蚨祥里找到。”张平说。
修复古籍是个漫长的过程。“修复一本破损几十页的书,就需要三五天。”古籍馆修复师小田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手头正在修复的是清代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天禄琳琅”,共有1000余册,“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但完全修好,大概要用近5年时间。”
与时间赛跑
在国图古籍修复室,不少如小田那样年轻的面孔,65岁的张平已经是师傅一辈了,但他依旧是活跃在国内古籍修复行业一线的中坚力量。张平说,他自己动手的机会比原来少了,“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带徒弟”,“虽说认识到了古籍修复是门科学,但论手上的功夫,那毕竟是种技能,它一定要靠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脱离不了。”
除了指导国图的年轻修复师,张平还在首都图书馆为6名古籍修复人员传授技艺,并在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湖北传习所和安徽省图分别带了四五名徒弟。
“我们算了一下,全国2800多家图书馆收藏的古籍藏量超过5000万册,其中1/3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张平说,按照目前国家图书馆的修复进度,一人一年可修复100册古籍,各地的情况均有不同。加上古籍一次修复的保持年限,这样算下来,“永远也修复不完”。人才的培养问题显得至关重要,但这其中,又存在诸多无奈。“古籍修复,是快与慢之间的交战,一方面是大量古籍等待抢救,慢不得。另一方面,是无论人才培养还是修复本身,都需要耐心和时间,快不得。”
古籍修复是一个与寂寞为伴的职业,需要经年累月的积累,需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毅力。采访最后,记者问张平如何能坐住这30年的冷板凳,“当你看到一本本残损的古籍,经过你的手,皱痕得以舒展、被虫蛀的缺失得以补齐,你延长了它的寿命,保护了文化,成就感就油然而生。”
除了“今人重见古时月”般的成就感,张平也有自己的独特乐趣,“工作时,我经常会想到道真和尚,他组织了有史料记载以来首次古籍修复。遥想他在补修佛经时的状态和场景,我会有种和古人对坐的感觉,很微妙。”言及此,这位整个采访中都不苟言笑的老人,露出笑意。(《环球人物》记者 卢楚函)




